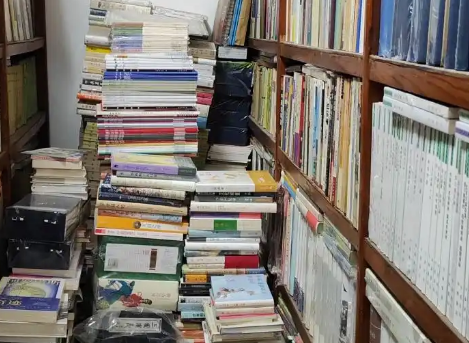在造纸术发明之前,书籍大部分是写在竹简上的,竹简很沉重,还容易被损坏,所以非常稀少,不易传播。国家也要建造专门的图书馆来收藏和保存书籍。
老子就是周朝的“守藏室之史”,也就是皇家图书馆管理员。孔子耗费一生心血,才整理出六经:《诗经》《尚书》《仪礼》《易经》《乐经》《春秋》,将它们传给学生。秦始皇大规模焚书之后,全国剩下的书籍寥寥可数。当时有个学者叫伏生,是孔子的学生宓子贱的后代,他把孔子传来下的《尚书》偷偷藏在墙壁中,但是因为秦末战争频繁,这本藏起来的《尚书》也损失了四分之三,只剩下二十八篇。
汉朝建立以后,汉文帝特意让学者跟从伏生学习《尚书》,伏生这时候已经九十多岁了,言语不清,由女儿羲娥代他说话,讲解残存的《尚书》,把他心中记得的部分也口述出来,这才把这部残缺不全的儒家经典流传下来。比起《尚书》的坎坷,《乐经》更可惜,已经永远消失在秦朝的战火之中了。可见书籍的脆弱与稀有。
东汉蔡伦改进了造纸术,纸张逐渐普及,为书写提供了方便,也使藏书成为普遍现象。不仅政府有“东观”“秘府”等皇家图书馆,当时的著名学者也都有私人藏书,比如汉末大学者蔡邕家里藏书万卷,当时人都很羡慕。大城市甚至还有了买卖书籍的“书肆”。但在印刷术发明之前,书籍无论是写在竹简上还是写在纸上,都全靠手抄传播,手抄费时费力,还容易有错误,所以书籍非常珍贵。

02 书籍始终是古人心中的“奢侈品”
唐代印刷术发明之后,大大促进了书籍的传播,政府藏书增加,私人藏书也很兴盛。但雕版印刷效率低,成本高,书籍仍然是奢侈品。普通人家有一本书就要奉若珍宝,贵族的藏书更是家族实力的象征之一。
当时贵族炫耀家世,“藏书”是必须提到的。比如我们课文上学过的诗人杜牧,在《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》中描述自己的家世:“旧第开朱门,长安城中央。第中无一物,万卷书满堂。”杜牧是名门之后,祖父是宰相,但他不夸耀其他,只夸耀自己家里书多,因为万卷书已经是家世地位的象征。唐朝有很多外国留学生,政府对他们很慷慨,食宿费全包,车马费全包,但唯一不包的就是书籍费,因为书籍实在太昂贵了。
即使宋代发明了活字印刷术,书籍成本再次下降,但仍然不是平民子弟可以说买就买的。我们课文中学过明朝初年的学者宋濂的《送东阳马生序》,宋濂写自己的求学之路:“余幼时即嗜学。家贫,无从致书以观,每假借于藏书之家,手自笔录,计日以还。天大寒,砚冰坚,手指不可屈伸,弗之怠。录毕,走送之,不敢稍逾约。”宋濂小时候热爱读书,但是家里穷,买不起书,只能借人家的书抄。大冬天砚台里的墨水都结冰了,手指冻得都伸不开,也不懈怠地抄书。抄完了赶紧跑着送回去,不敢逾期,怕人家下次不借。可见一直到了明朝初年,相比较其他商品来说书籍仍然很昂贵。直到明朝中期以后资本主义经济萌芽,出版业空前发达,书籍供应量剧增,价格才开始下降到普通人可以随手买一本的程度。
03 文字自诞生就带着一股神力
除了经济成本昂贵之外,书籍在古代人心理上也很珍贵,这出自古人对文字和知识的敬畏。传说仓颉造字的时候,天雨粟、鬼夜哭。文字从诞生就带着一股神力,因为文字代表着知识,而知识是宝贵的。
上世纪的农村还能看到有“敬惜字纸”的标语和焚烧字纸的敬字炉。写了字的纸不能随便乱扔,或者擦脏东西,否则就是亵渎,要专门在敬字炉里焚化。对字纸尚且如此,对书籍就更是爱惜。从政府到民间,都有很多著名的藏书楼。古人要读一本好书,往往还要焚香沐浴,恭恭敬敬拜上一拜再读。
中世纪的西方恰恰相反,文字在人们心目中不是带着神力而是带着魔力,因为教会把宗教中异端的兴起和宗教的分裂归罪于书籍,把知识和魔鬼挂上等号,读书就是着魔,拥有丰富的知识就是魔鬼附体。和我国古代人们对知识和书籍的顶礼膜拜恰好是两个极端。高尔基说:“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。”我们今天获取书籍非常方便,无论是书店里的实体书,还是网络上的电子书,都堪称浩如烟海。书籍在人们心中也不再像古代那么珍贵,因为大量娱乐性读物的存在,读书甚至成为休闲娱乐的一部分。每个人对读书的看法都不一样,但是多读书、读好书,永不间断地进行自我教育,应该成为我们生活的惯性。
作者简介
孔燕妮:
复旦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博士,资深编辑、撰稿人。
本文来源
选自读者·新语文出品的人文素养养成类课程《古诗文中的服饰漫谈》。深入了解古诗文背后的制度和文化,是让古诗文“活”起来的一条必经之路,在这个系列的课程中,让我们走进古诗文中的古人生活,通过古诗文来复活历史、复活文化,从充满温度的历史细节中来了解古人的思想感情、生活习惯和价值取向。只有真正走进古人的生活,才能真正了解古代的文化,理解“活”的古诗文。
相关文章